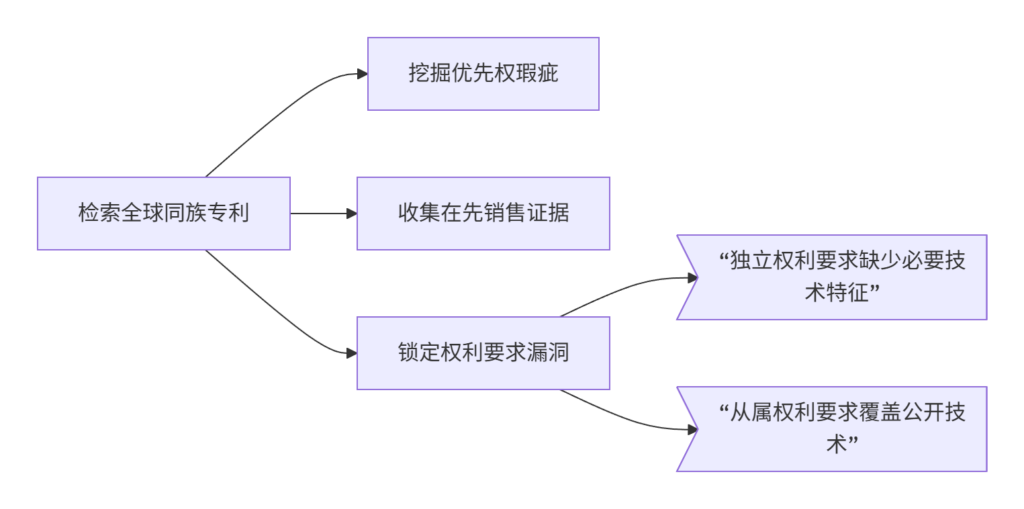专利无效宣告程序是指自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告授予专利权之日起,任何单位或个人认为该专利权的授予不符合专利法规定的,可以请求专利复审委员会宣告该专利权无效的制度,专利无效宣告程序是为避免不当授权的专利损害社会公众利益而设置的一种纠正程序。在专利无效宣告程序和后续的专利无效行政诉讼程序中,公知常识的认定和举证责任分配会对案件结果产生重要影响。本文通过对现行法律法规和典型司法案例分析研究,形成以下作者观点。
一、公知常识的认定
(一)公知常识的基本定义
《专利审查指南(2023版)》第四部分第八章第4.3.3节,当事人可以通过教科书或者技术词典、技术手册等工具书记载的技术内容来证明某项技术手段是本领域的公知常识。
《专利审查指南》等相关规定并没有对公知常识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结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司法案例,公知常识通常指的是本领域的教科书、技术手册或工具书中披露的解决特定技术问题的技术手段,或者是本领域中解决特定技术问题的惯用手段。
(二)公知常识性证据的认定要件
一般而言,对于相关技术手段是否属于公知常识,原则上可以通过技术词典、技术手册、教科书等所属技术领域中的公知常识性证据加以证明,如无相反证据,技术词典、技术手册、教科书记载的技术知识可以推定为公知常识。对于公知常识性证据的认定,可从以下三方面考虑。
首先,需审查该文献的公开时间及所属领域。文献公开日应早于涉案专利的申请日或优先权日且应与涉案专利的技术领域相同或相近。
如(2021)最高法知行终500号判决中认定,本案二审期间当事人提交的新证据8-9的公开日晚于本专利申请日,不能证明涉案专利申请日之前的现有技术状况。
其次,从载体形式上需审查相关文献是否属于图书,图书应仅有ISBN书号。
如(2020)最高法知行终35号判决中认定,《肿瘤研究前沿》第8卷的图书在版编目(CIP)显示其书号为ISBN978-7-81086-559-3,ISBN是国际标准书号的代称,在我国已使用多年,故应当认定《肿瘤研究前沿》第8卷属于图书。
最后,审查该图书的名称、封面、扉页、或者序中是否明确载明“教学用书”、“教材”、“词典”、“辞典”或“手册”等字样。
如有明确记载,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通常可以认为其属于专利法意义上的公知常识性证据。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节选,国家药典委员会编,2010年版;《中国药品检验标准操作规范》节选,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0年版”在判决中均被最高院认定为公知常识性证据。
如无明确记载,可从图书封面、序言、前言等记载的内容以及受众、传播范围进行分析。如在(2021)最高法知行终44号判决中认定,1999年版《工业产品着色与配色技术》从该书封面及“前言”所记载的内容来看,该书由中国轻工业出版社1999年出版,其中介绍了在不同基质材料上的着色与配色、着色剂的要求和选择、配色与配方等,书籍中“内容新颖、详实”,受众主要是与着色有关的行业人员,该书并不属于教科书、技术词典、技术手册,结合其载体形式、内容及受众,亦无法认定为属于记载本领域基本技术知识的公知常识性证据。
(三)除公知常识性证据外其他类型文献的证明标准
专利无效案件中有时会存在相关技术手段难以通过技术词典、技术手册、教科书等公知常识性证据予以证明的情况,此时可以通过所属领域的多份非公知常识性证据例如多篇专利文献、期刊杂志、图书等,结合该文献的载体形式、内容及其特点、受众、传播范围等具体认定,但这种证明方式应遵循更严格的证明标准。
如(2021)最高法知行终472号判决中认定,在难以通过技术词典、技术手册、教科书等公知常识性证据予以证明的情况下,也可以通过所属领域的多份非公知常识性证据,例如多篇专利文献、期刊杂志等相互印证以充分说明该技术知识属于公知常识。被诉决定引用了三篇专利文献,目的在于进一步对在固定支承膝关节假体中,通过胫骨盘和支承件连接部之间的凸凹轮廓互补使得两者咬合锁定从而达到固定连接的目的是所属技术领域的常规技术手段进行合理的说明,这种进一步加强说理的论证方式并未违反创造性评价的原则。
(四)惯用手段的证明标准
对于惯用技术手段,除采用第(二)项、第(三)项的证明方式外,通过说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在现有技术的基础上仅仅通过合乎逻辑的分析、推理或者有限的试验可以得到,即使没有证据佐证,也可以认定某一项特征为惯用手段。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授权确权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一)》(2020修订)第二十八条规定,当事人主张有关技术内容属于公知常识或者有关设计特征属于惯常设计的,人民法院可以要求其提供证据证明或者作出说明。《专利审查指南(2023版)》第二部分第四章第2.2节,“如果发明是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现有技术的基础上仅仅通过合乎逻辑的分析、推理或者有限的试验可以得到的,则该发明是显而易见的,也就不具备突出的实质性特点。”
如(2023)最高法知行终715号判决中认定,如果某些技术特征是本领域普遍应用的有限手段,则通常应认定其为本领域的常规选择,一般不足以使相关专利或专利申请具备创造性。
二、公知常识的举证责任和举证期限
(一)专利无效宣告程序,公知常识证据的举证责任和举证期限
《专利审查指南(2023版)》第四部分第八章第4.3.3节,主张某技术手段是本领域公知常识的当事人,对其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该当事人未能举证证明或者未能充分说明该技术手段是本领域公知常识,并且对方当事人不予认可的,合议组对该技术手段是本领域公知常识的主张不予支持。因此,专利无效宣告程序中,公知常识的举证责任原则上由主张某技术手段是本领域公知常识的当事人承担。
《专利审查指南(2023版)》第四部分第八章第4.3.1节,(1)请求人在提出无效宣告请求之日起一个月内补充证据的,应当在该期限内结合该证据具体说明相关的无效宣告理由,否则,合议组不予考虑。(2)请求人在提出无效宣告请求之日起一个月后补充证据的,合议组一般不予考虑,但下列情形除外:(ii)在口头审理辩论终结前提交技术词典、技术手册和教科书等所属技术领域中的公知常识性证据或者用于完善证据法定形式的公证文书、原件等证据,并在该期限内结合该证据具体说明相关无效宣告理由的。因此,在专利无效宣告程序,对于技术词典、技术手册和教科书等所属技术领域中的公知常识性证据,无效宣告请求人和专利权人均可以在口头审理辩论终结前补充。
如(2020)最高法知行终406号判决中认定,在口审时,一方当事人当庭提交的“证据10:《新能源材料》,雷永泉主编,天津大学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证据11:《化学电源》,吕鸣祥等编,天津大学出版社,1992年9月第一版,1998年6月第二次印刷。”另一方当事人提交的“反证1:GB/T18287-2000国标《蜂窝电话用锂离子电池总规范》复印件,2000年12月28日发布。”国家知识产权局对上述证据分别转送对方当事人,当事人均当庭签收,经质证予以采纳。其中对当庭提交的“国家标准《蜂窝电话用锂离子电池总规范》”,国家知识产权局认为该国家标准具体涉及了蜂窝电话用锂离子电池的各项参数,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锂离子电池领域的技术状况,可以作为公知常识性证据在口头审理辩论终结前补充。另在(2019)最高法知行终124号判决中认定,在口审时当事人当庭提交的“国家标准GB/T15969. 1-2007/IEC61131-1: 2003。”国家知识产权局也予以采纳。经上述分析,对于某一行业或领域的国家标准,也可适用例外情形在口头审理辩论终结前提交。
如果使用非公知常识性证据证明公知常识,建议无效宣告请求人将其作为一般性证据在提交无效宣告请求时或者在提交补充无效理由的一个月举证期限内提交。
如在(2020)最高法知行终424号判决中认定,“关于附件49、52。某电脑上海公司于提出无效宣告请求时仅提交了附件3、附件18的文档复印件,其并未显示公开日期。某电脑上海公司于无效宣告请求日起一个月内并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附件3、附件18的公开日期。附件49、52系邮件归档页面和索引页面的截图打印件及其中文译文。某电脑上海公司于无效宣告请求日起一个月后提交的附件49、52,增加了有关公开日期的关键信息,不属于对附件3、附件18形式上的完善,而系新的证据。”上述补充提交的证据以公证书的形式提供了关于公开时间信息等新的实质性证明内容,应受到一个月的举证期限的限制,在超出该举证期限提交的情况下不应予以接受。专利复审委员会对上述超出无效请求日起一个月的新的证据不予接受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于合议组而言,在合议审查中,合议组可以引入所属技术领域的公知常识,或者补入相应的技术辞典、技术手册、教科书等所属技术领域中的公知常识性证据。
(二)专利无效行政案件中,公知常识证据的举证责任和举证期限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授权确权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一)》(2020修订)第二十八条规定,当事人主张有关技术内容属于公知常识或者有关设计特征属于惯常设计的,人民法院可以要求其提供证据证明或者作出说明。在专利无效行政诉讼中,公知常识的举证责任由主张某技术手段是本领域公知常识的当事人承担。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授权确权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一)》(2020修订)第三十条规定,无效宣告请求人在专利确权行政案件中提供新的证据,人民法院一般不予审查,但下列证据除外:(一)证明在专利无效宣告请求审查程序中已主张的公知常识或者惯常设计的。因此,无效请求人可以在专利无效行政案件中提交在专利无效宣告请求审查程序中已主张的公知常识的证据。对于无效请求人,如提供的是非公知常识性证据,原则上法院不会采纳。
如(2023)最高法知行终307号判决中认定,某甲公司上述证据并非教科书或者技术词典、技术手册等工具书,其本身不属于公知常识性证据。《专利审查指南》第四部分第八章4.3.3节规定当事人可以通过教科书或者技术词典、技术手册等工具书记载内容证明某项技术手段为本领域的公知常识,是基于工具书证据的权威属性为本领域技术人员所公认。某甲公司一审提交的证据8-13期刊论文仅为作者发表的个人观点,一审法院认定其不属于公知常识证据,不予审查,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授权确权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三十条的规定,本院予以确认。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授权确权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一)》(2020修订)第二十九条条规定,专利申请人、专利权人在专利授权确权行政案件中提供新的证据,用于证明专利申请不应当被驳回或者专利权应当维持有效的,人民法院一般应予审查。因此,专利权人可以在专利无效行政诉讼阶段提交公知常识相关证据。
如(2020)最高法知行终564号判决中认定,专利确权行政诉讼中,国家知识产权局在二审中提交了一份审查决定和专利文献作为新的证据。对于该新证据最高法院的认证意见为:虽然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的上述证据1和2并非其作出被诉决定的依据,但考虑到专利确权程序系特殊的行政程序,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上述证据主要系针对一审判决所提及的当事人陈述前后矛盾这一新事实,其证明目的是涉案专利权应当被维持有效,否则专利权人将丧失救济机会,故本院对于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上述证据予以审查。
在专利无效宣告程序和专利无效行政案件中,公知常识的举证责任分配和举证时限设定,在公平价值与效率原则间寻求动态平衡,既保障了专利无效宣告请求人、专利权人及行政机关等主体的程序参与权,又通过合理的时限规制维护专利制度的权威性与稳定性。
(本文作者:盈科王柱、崔德宝律师)